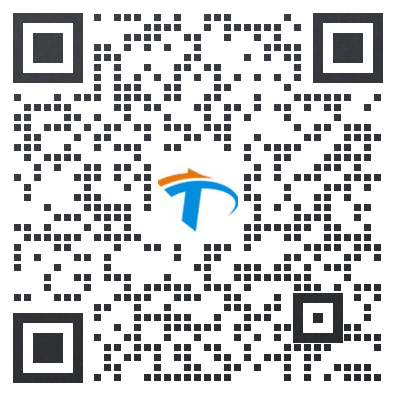|
漫天的蒼蠅
我?guī)е梦埠油摹陡Q視印度》一齊到了北印。那是他在1983年寫的作品,二十多年后,我在他寫過的畫過的城市里停留,發(fā)現(xiàn)時(shí)光似乎就此凝固。舊德里、齋浦爾、阿格拉、瓦倫納西,似乎都沒有什么變化,街道還是那么擁擠,人們還是那么喜歡嚼檳榔,蒼蠅還是那么多,街頭小吃還是那幾個(gè)花樣。對(duì)于旅行者,這也許是不錯(cuò)的機(jī)緣,可是對(duì)當(dāng)?shù)厝藖碚f,并不是太好的事情。
妹尾河童在書里非常推薦街邊的咖喱餃子,惹得我一直想吃。但是,從德里開始,到齋浦爾,到阿格拉,我一路追尋,都沒有吃成。不是沒有,而是,太臟了。眼見著蒼蠅叮在上面,然后飛走,然后又駐足,怎樣都入不了口。
街頭亦有很多水果攤,黃瓜也是其中熱銷的品種之一。小販總喜歡把黃瓜皮削掉,讓瓜肉赤裸在陽光下,引來蒼蠅無數(shù)。但印度人似乎毫不介意,照樣喜歡買。買了以后,小販會(huì)把黃瓜剖成兩半,然后在黃瓜瓤上撒些咖喱粉,再遞給買主。而買主,接過來就往嘴里送了。
我們不敢。喝的水全是買來的瓶裝礦泉水,吃飯的地方總也選擇那種看上去比較干凈的餐廳,雖然貴,總好過拉肚子吧。但僅僅吃了幾天,我的胃就開始抗議了。印度人實(shí)在是太喜歡用香料,很多種香料混在一起,散發(fā)出很奇怪的香氣,把菜的原味完全遮掩,吃到嘴里全然不知道為何物。看不到印度飛餅,沒有純粹的咖喱風(fēng)味,除了酸奶和馕覺得很好吃,其他的無論是蔬菜還是非蔬菜,每到點(diǎn)餐的時(shí)候,我就發(fā)愁。以至于到最后幾天,我看到必勝客、麥當(dāng)勞和肯德基,就像見到了老鄉(xiāng)一樣,欣喜若狂。
其實(shí),即便是在這些非常西化的快餐廳里,也能見到蒼蠅,只不過是少許多,心里尚能接受。就像肯德基在中國有老北京雞肉卷,在印度,洋快餐們也進(jìn)行了入鄉(xiāng)隨俗式的改良,有純素的蔬菜卷,也添加了一些魚類品種。在必勝客吃匹薩的時(shí)候,我還特別留意了印度人是否真的不會(huì)用左手拿食物。但眼睛所看到的是,多數(shù)人都是兩只手拿著匹薩吃。
砍價(jià)的樂趣也許是因?yàn)樯僖姈|亞人,每到一個(gè)地方,我和David走在街頭總能招來百分百的回頭率。有人朝你微笑,Sayhello,還有人問What'syourname?最有意思的是某個(gè)傍晚在瓦倫納西,天色已黑,我和David在小城里晃蕩,迎面走來一個(gè)穿著傳統(tǒng)印度服裝的男人,50歲上下的樣子,突然就在David的面前站定,一言不發(fā),伸出手來。David下意識(shí)地也伸出了手,印度男人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,然后,又一言不發(fā)地走了。
在司機(jī)的帶領(lǐng)下,我們分別去過不同城市的幾個(gè)私人手工作坊。在那些作坊里,我們參觀過工人如何織布,如何給布進(jìn)行植物印染,如何織地毯,如何打首飾,如何做樂器,如何畫工藝畫以及如何制作大理石工藝品等等,倒也有趣。最后的環(huán)節(jié),通常是作坊里的導(dǎo)游帶我們到購物房里挑選產(chǎn)品。
若是碰到有喜歡的,必然會(huì)經(jīng)歷長長一段砍價(jià)。通常,我攔腰砍斷,見到的肯定是印度人吃驚的表情。“不,這是不可能給到的價(jià)格。”他們總是這么說。我堅(jiān)持。然后他們會(huì)說:“好吧,我給你這個(gè)價(jià)。”我搖頭:“不,我堅(jiān)持要我剛才的價(jià)格。”“小姐,這個(gè)價(jià)格實(shí)在是太低了,我們不能給你,或者,我給你這個(gè)價(jià)格,它已經(jīng)非常低了。”我再次搖頭……
到現(xiàn)在,我也不知道我買的東西到底算便宜還是算貴,總之折算成人民幣似乎并不算很便宜,但百分百的印度feel,讓我喜歡。
粉紅色的齋浦爾
印象最好的城市是齋浦爾。尤其是清晨時(shí)分,大多數(shù)店鋪關(guān)閉著,清冷的路邊,身穿紗麗頭頂水罐的女郎,走在水車過后留下的濕轍印上,還沒容人細(xì)看,婀娜多姿的身影便消失在粉紅巷子深處;空氣里混合著的清新花香,趕早的花攤一字排開,美艷的金盞花和清麗的茉莉,用棉線繞出長長的花串,等著祭神的人來買……金紅的晨暉下,一座城的繁華延綿到了古廟里,虔誠的教徒那么多,在祈禱或吟誦。
和印度其他古城不同,齋浦爾有著良好的城市規(guī)劃和筆直寬闊的大街,這要?dú)w功于三百年前那位天才的王公薩瓦伊·杰伊·辛格二世(SAWAIJAISINGHII),作為莫臥兒皇帝奧朗則布(AURANGZEB)最重要的廷臣,他不僅是那個(gè)年代偉大的政治家、武士、梵文和波斯文學(xué)者,還是偉大的天文學(xué)家和建筑師,齋浦爾就是在他的規(guī)劃下修建起來的,時(shí)至今日,齋浦爾仍然是全印度最美的城市之一。
不過齋浦爾城的粉紅基調(diào)是來自后來的薩瓦伊·羅摩·辛格(SAWAIRAMSINGH)王公。為了歡迎當(dāng)時(shí)還是威爾士王子的愛德華七世,王公下令將城中所有房子面街的一面刷成粉紅色。據(jù)說當(dāng)時(shí)有綠、黃和粉紅等好幾種顏色候選,最后還是選擇了粉紅色,因?yàn)樵谟《热说纳收Z言中,粉紅代表著好客。至今,齋浦爾在法律里還有著臨街房屋必須保留刷粉紅色的規(guī)定。
齋浦爾市內(nèi)有一座非常華麗的“風(fēng)之宮殿”,對(duì)面則是由密密麻麻小檔口組成的集市,販賣廉價(jià)的印度服飾。這種構(gòu)成,讓齋浦爾市中心呈現(xiàn)出了一種很特別的面容:華麗和平民是如此地相輔相成,互相映襯。
黃昏時(shí),一定要到東面的小山上去,站在太陽廟(SURYYMANDIR)前的石板平臺(tái)上遠(yuǎn)眺齋浦爾古城。夕陽的光線下,齋浦爾猶如一塊寶石,閃爍著魔幻般的粉紅光芒。那一刻,就像路邊的眼鏡蛇在弄蛇人的魔笛聲中歡樂起舞,我的心也迷失在粉紅之城的光影中。
恒河邊的瓦倫納西
這是一個(gè)位于恒河之畔的圣城,貧富差別非常懸殊。富人的別墅區(qū)種滿了芒果樹,干凈而漂亮。靠近恒河的地方,是普通市民居住的小房子,臟且亂,悶熱的空氣中還時(shí)刻飄著尿的騷味——印度男人毫不顧忌地當(dāng)街如廁,那些公廁是露天的。
到瓦倫納西的第二天,為了一睹晨浴的神圣,清晨四點(diǎn)半,我們走出了酒店,朝恒河邊走去。
一路走過,街上到處是人,躺著的人。他們大多還在熟睡,有些蜷縮在地面上,旁邊可能同時(shí)蜷縮著一只大黃狗;也有蜷縮在人力車上的,也許那車便是他們惟一的家當(dāng)。在微弱的天色中,穿過這樣的街道,我的心里很不好受。也就是從那天清晨起,我再?zèng)]有為5盧比10盧比和人力車夫討價(jià)還價(jià),且總會(huì)光顧老一點(diǎn)的車夫,雖然他們的速度會(huì)慢一些。
五點(diǎn)鐘的恒河畔,已經(jīng)十分熱鬧。賣花的、賣蠟燭的、賣水的、賣吃的,還有招攬游船生意的,見到旅行者模樣的人,就上來搭訕。我們租了一只小船,撐船的是一個(gè)15歲的孩子。
漸漸地,來晨浴的人就多了起來。彼時(shí),我們的船已經(jīng)撐到河中央,使得我們能恰到好處地觀看晨浴。來沐浴的人,大多是男人,在岸邊脫去上衣和長褲,穿一條內(nèi)褲往河中走,也有不脫衣服或全裸上陣的,大家都是那么自然。也有婦女,紗麗不摘,浸浴在河水中,在泛白的天空下宛若圣潔的女神。
恒河不寬,兩岸卻有著天壤之別。一岸廟宇繁華無限生機(jī),一岸則是荒涼的沙地,人煙全無。我們的船就這樣行駛在繁華和荒涼之間,一段一段地看兩岸不同的風(fēng)景。有人在沐浴時(shí)往河水里吐痰,有人在岸邊的石頭上做瑜伽,還有人圍著火堆在轉(zhuǎn)圈。“看,他們?cè)跓?rdquo;撐船的孩子對(duì)我們說。我的心一抖,可他的表情,是那樣平靜。“你們?nèi)粝肟锤嗟臒梢酝砩蟻怼5遣灰恼铡?rdquo;
拉納西,生死都在恒河邊
那個(gè)晚上,我們真的又到了恒河。沒有坐船,而是沿著繁華的河岸一直散步。走啊走,就走到了燒尸的區(qū)域。我看著那具被白布包裹的尸體被抬進(jìn)了木堆里,然后剃光了頭的兒子親手將木堆點(diǎn)燃。熊熊大火燃起,兩三個(gè)小時(shí)后,地球上的一個(gè)軀殼將消失殆盡。
我站著靜靜地看了十分鐘,心里泛起一種莫名的異樣感覺,然后想起早晨那個(gè)孩子平靜的眼神以及平靜的語氣,轉(zhuǎn)身離去。
遠(yuǎn)遠(yuǎn)地,聽到一陣熟悉的吟唱,那是在廣州時(shí)印度瑜伽老師教我們唱的五字歌謠。在歌聲里我回頭再看恒河,波瀾不驚的河水有了一種早晨我不曾感受到的神圣。 |